遲到的謝師宴文/應(yīng)紅楓 中化興中 |
|
在每個男人的內(nèi)心,都有一份知恩圖報的良知,只是在自己力所能及之前,只能沉默著努力奮斗 2017年春節(jié)前夕,38歲的陳濤從深圳回來祭祖,并在舟山群島金塘老家的祖堂前舉辦了婚禮。這個年齡的單身漢,按流行的說法,是屬于“齊天大剩”了。 按照漁村的風(fēng)俗和規(guī)矩,陳濤邀請了同族的長輩、堂兄及當(dāng)?shù)氐挠H朋好友,在祖堂前辦了十幾桌族酒,并舉行了拜堂儀式。所謂族酒,是宴請同族村民及至親鄉(xiāng)鄰,可以不送紅包,氛圍比較寬松。但有一個拜堂敬茶環(huán)節(jié),卻是嚴(yán)格按輩分次序排座,不可亂了規(guī)矩。那天,在原本應(yīng)該是父母大人就坐的座位上,坐了一位略顯蒼老的婦人。賀喜的族親們都感到奇怪,既然那不是陳濤的母親,又怎能被邀請來坐在母親的位置上呢? 陳濤的母親,是一位苦命的漁家婦女。陳濤的父親是一個粗壯的漁家漢子,卻在陳濤年幼的時候,下海捕魚不慎落海,直到現(xiàn)在,山坡上留的還是一座衣冠冢。從小到大,娘倆相依為命,靠母親在漁村里理網(wǎng)、幫魚販剖魚鲞打些零工,把他拉扯長大。陳濤自小性格倔強,最痛恨別人叫他沒爹的孩子,為此沒少和別的孩子打架,也多次被老師告到家長那里。 小學(xué)四年級那年,班主任章鈺老師在家訪時羅列了陳濤在學(xué)校的“十大罪狀”。陳濤母親在老師面前沒說什么,只是一個勁兒賠不是。待老師走后,母親對著丈夫的遺像,整整哭了大半夜。那一夜,陳濤也沒有睡,抱著母親的肩膀,哭得撕心裂肺……那一夜,他感覺自己突然長大了,感覺到他有責(zé)任撐起這個家,不再讓母親一個人孤苦無依。第二天,他對母親說,不再上學(xué)了,要去打工,多少能夠賺錢補貼家用。 章鈺老師向陳濤母親告狀后,也知道了當(dāng)晚娘倆抱頭痛哭的事。面對這個沒爹的孩子,章鈺老師心生愧疚,多次趕到陳濤家里勸說,拉回了打算退學(xué)的陳濤,還向陳濤母親要了一張他父親的照片。 回到學(xué)校的第三天放學(xué)后,章鈺老師和陳濤進行了一次長談,足足有兩節(jié)課的時間。不知道具體內(nèi)容,只是有同學(xué)看見,陳濤淚眼婆娑地跪在地上,桌上放著他父親的那張遺照。章鈺老師也眼含淚水,使勁地想拉他起來,拉不動。 自此以后,陳濤像換了個人,變得沉默了。章鈺老師也改變了對他的態(tài)度,經(jīng)常留他在學(xué)校吃晚飯,輔導(dǎo)作業(yè)也給他開小灶。生活上,更是對他關(guān)懷備至,陳濤身上穿的很多衣服、襪子,都是章鈺老師給買的。一天中午下課,陳濤剛要走出教室門,被章鈺老師叫住:“陳濤,你的頭發(fā)這么長,去理一理吧!”陳濤紅了臉,答應(yīng)了老師。可下午回來時沒理,第二天還是沒理。章鈺老師晚上放學(xué)前又叫住了陳濤,陳濤難為情地低下頭:“媽媽讓我等她發(fā)了工錢再去理發(fā)。”章鈺老師二話沒說,拉著陳濤來到了學(xué)校旁邊的理發(fā)店,給他理了個漂亮干凈的學(xué)生頭。 五年級下半學(xué)期,學(xué)校對學(xué)生進行體育達標(biāo)考核,陳濤在沙坑跳遠的時候,不小心沙子濺進了眼睛里。陳濤也沒說,直到眼眶紅腫成嚴(yán)重結(jié)膜炎。那幾天,陳濤沒有在自己家里休養(yǎng),而是在學(xué)校章鈺老師的宿舍外間搭了張床。老師像照顧自己孩子一樣照看他,每天按時給他換藥膏,燒好飯菜給他喂飯,并抽空給他補課。 愛的付出,終有回報。陳濤以全年級第二的成績畢業(yè),被學(xué)校保送進入縣城初中讀書。但是命運似乎專門和陳濤過不去,在他進入縣城初中的第二年下半學(xué)期,他母親突然一病不起,拖了幾個月,竟然撒手而去。相依為命的母親走了,陳濤的天塌了下來,唯有的堂叔和堂舅也不太愿意接收撫養(yǎng)他。這時,有一個人來了,表示愿意撫養(yǎng)陳濤。這個人就是章鈺老師。這一年,陳濤剛好15歲。 時間過得很快,一晃,陳濤初中畢業(yè)了,卻死活不肯再上高中,堅決不要再花章鈺老師的錢去讀書。章鈺老師反復(fù)做他的思想工作,但是陳濤主意堅決,一定要去找一份工作養(yǎng)活自己。 漁村里的鄉(xiāng)民們都知道陳濤的身世,一些張網(wǎng)戶還會給陳濤一些分揀小魚小蝦的活計,給他一口飯吃。家里的日常生活起居,還是章鈺老師照應(yīng)和接濟。 這樣苦熬了兩年,陳濤出落成了一個俊朗的小伙子。19歲那年,他通過別人介紹,到一艘漁船上做幫工,出海捕魚去了。第二年冬季,他在捕撈船上當(dāng)網(wǎng)手時,左手三個手指被絞纜機絞得像壓扁了的蘿卜干,從此再沒出海。 斷了生活來源,陳濤又只好給一些張網(wǎng)戶打起零工來。但是那樣打零工收入少,僅夠糊口,不是長久之計。沒幾個月,他打理好包袱,獨自南下尋生計去了。 這一去,陳濤將近二十年杳無音訊。這一次突然回來,大出鄉(xiāng)鄰們的意料。聽陳濤說,這些年,自己像豬狗一樣爬過來,現(xiàn)在在深圳組建了幾家合資企業(yè),并成為一家有相當(dāng)規(guī)模的企業(yè)的一把手。他帶來的新娘,據(jù)說是蘇州人,端莊淑雅,舉手投足間透著江南女子的知性之美。 婚禮的敬茶環(huán)節(jié),陳濤敬的第一位長輩,是在陳濤堅持下坐上母親席位的章鈺老師。新娘恭恭敬敬地端著茶盤,陳濤身著婚禮盛裝,端起一杯香茶,送到了章鈺老師的手上。章鈺老師也蒼老了,兩鬢都已經(jīng)有了些許白發(fā),端著茶杯的手,微微有些顫抖。 陳濤凝視著章鈺老師,突然握住老師的手,跪了下來,低下頭,忍不住哭出聲來。章鈺老師顯然有些意外,忙站起來拉住陳濤:“傻孩子,你這是做什么?今天可是個喜慶開心的日子啊!”陳濤不肯站起來,如當(dāng)年在教室里跪在父親遺照前一樣,哭得像個孩子。陳濤對章鈺老師說:“二十多年前,您像母親一樣對我有養(yǎng)育之恩,像母親一樣一口一口地喂我吃過飯,我卻從沒對您說過一句感謝的話。今天我回來,不僅是想在我的婚禮上,體體面面地請您吃一頓飯、給您敬一杯茶,我還有一個心愿:讓我叫您一聲干娘吧!”說完,陳濤再次俯下身去,在祖堂前的石板地上,給章鈺老師“咚、咚、咚”磕了三個響頭。 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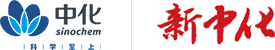




 建議(1024*768) IE7.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
建議(1024*768) IE7.0以上瀏覽器瀏覽本站




